新時代中國刑事執行法學三大前沿熱點問題
2024-12-13 16:46:20 來源:法治日報·法治周末
■新時代刑事執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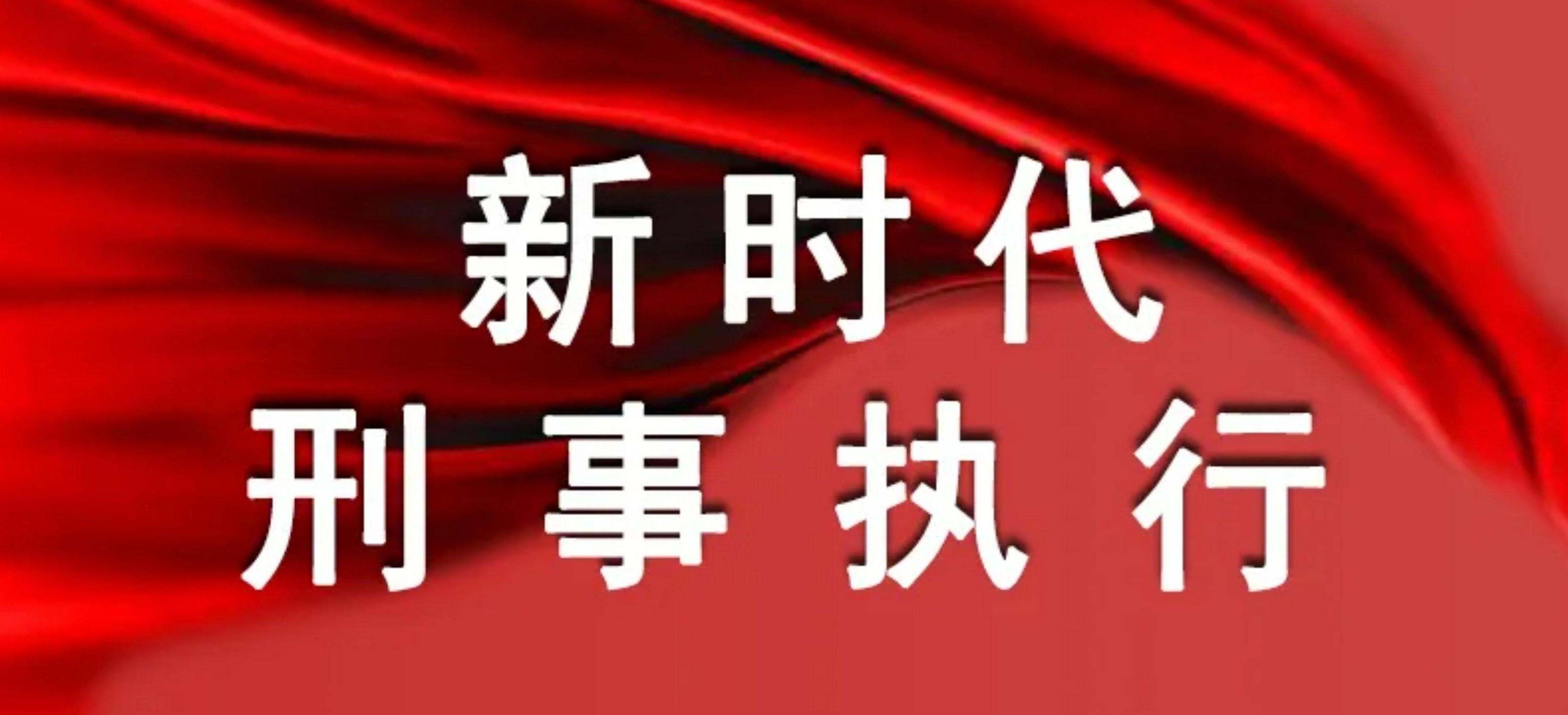
■欄目主持人 時延安 仇飛
投稿郵箱:fzzmhlw@legaldaily.com.cn
□劉曉梅
近日,天津市法學會犯罪學分會2024年年會暨“新時代刑事執行工作現代化”研討會、中國犯罪學學會第三十三屆學術研討會“犯罪防控對策與罪犯矯正”平行論壇、西北政法大學首屆刑事執行論壇等多個活動召開。
筆者通過組織、參加以上活動,梳理總結了理論界和實務部門共同關注的3個刑事執行法學熱點問題,即監獄法的修改與完善、刑事執行檢察監督的邊界和社會力量參與社區矯正的困境與出路。
監獄法的修改與完善
《中華人民共和國監獄法》自1994年12月施行至今已30年,監獄法誕生于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在改革開放的時代大背景之下,監獄法為實現“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提供了穩定的社會發展空間。
監獄作為刑事執行的主要場所,其在監獄法的規制之下逐步形成了“規范化、法治化、證據化”的管理運行機制,其充分實現了“收得下、管得住、跑不了”的目標設定,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之下發揮了舉足輕重的正向價值。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成功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偉大歷史轉折。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結構的變遷,犯罪模式和罪犯結構相較監獄法制定的時代有了較大的變化。為了適應形勢發展變化的需要,解決長期困擾監獄機關的急難愁盼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將監獄法的修改正式列入了立法規劃。
刑事司法活動包含“偵查、起訴、審判、執行”等環節,刑事執行作為刑事司法活動的收尾環節,其現實質效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刑事司法的最終效果。因此,理清監獄法與刑法、其他部門法之間的關系變得尤為重要,需將監獄法放置于新時代法律總體框架之中,以體系化的視角重新審視其立法目的、立法宗旨、制度設定等具體方面,將“行為矯正+回歸社會”的罪犯改造觀念融入法律文本與體制機制之中,讓罪犯在脫離原有行為方式的同時,能夠充分獲得回歸社會所需的生存技能,以達到有效改造的目的。
監獄法的修改與完善應當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導,立足于新時代法治實踐,堅持問題導向,著眼于監獄實務工作中的現實困難與需要。就其著力方向上具體而言,應當關注以下方面:
創新監獄監管模式,區分輕型與重型罪犯類型采取不同改造措施分類施治,減少交叉感染現象滋生;引入社會學、犯罪學等相關學科矯治手段,以綜合手段促進罪犯有效改造;融入新興技術手段參與監獄罪犯再犯罪風險評估,并將減刑、假釋證據化要求融入法律規范之中;堅持權責統一的基礎之上,賦予監獄充分管理自主權,并將其程序性制度設定上升到法律層面。
通過本次對監獄法的修改助推刑事執行工作現代化,希冀一部嶄新的監獄法不久即將問世。
刑事執行檢察監督的邊界
刑事執行檢察由監所檢察發展而來,其制度設計的初衷在于對羈押、監禁區域中刑事執行機關行使執行權的行為進行監督,在有效發揮刑法懲罰犯罪功能的基礎上,以期最大限度實現對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等被羈押、監禁主體的人權保障。
隨著刑事強制手段的多樣化發展,刑事執行檢察監督的職能逐步擴展為刑事執行監督、刑事強制措施執行監督、強制醫療執行監督等方向。在2004年人權入憲的頂層設計之下,刑事執行檢察監督充分發揮了其制度機能,有效實現了人權保障的職責使命。
刑事執行檢察監督職能范圍的擴大在發揮其正向價值的同時,實踐中出現“刑事執行與刑事執行檢察監督邊界不清、監督泛化、監督質效不佳”等問題,其癥結原因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監督職權法律依據原則化、矛盾化問題較為突出,刑事執行檢察監督操作空間大;駐所檢察天生具有內部監督屬性,易導致角色同化,監督形式化;監督職責泛化、復雜化與人員配置不足存在尖銳矛盾。
刑事執行與刑事執行檢察監督的邊界模糊直接導致兩者職責異化、刑事執行權喪失有效制約、人權保障失位等痹癥。因此,理清刑事執行權與監督權的邊界成為亟待破解的難題。
檢察機關是法定的法律監督部門,理清刑事執行與刑事執行檢察監督的邊界有助于疏通刑事執行檢察監督所面臨的痛點與堵點,是有效落實憲法賦予檢察機關法律監督權的關鍵,也是加快促進刑事執行現代化發展的必然要求。
在職責使命角度,應當堅定立足于刑事執行與刑事執行檢察監督各自制度目的。刑事執行即監獄、看守所等法定刑事執行部門依照有權機關作出的生效法律文書,將其具體實施的活動。刑事執行檢察監督則是檢察機關依照憲法與法律,對刑事執行主體實施生效刑事法律文書活動的合法性進行監督活動。
執行機關針對生效法律文書所指向的對象負監管責任,檢察機關應當立足于法律監督機關的職責定位,僅對執行機關履職行為的合法性與合理性進行監督,不應越位干涉執行機關的監管活動,更不可代執行機關行使監管責任。
在體制機制角度,應當靈活運用“派駐+巡回”檢察監督手段。刑事執行檢察監督脫胎于監所檢察監督,其天生具有執法與監督二者融合傾向。鑒于此,應當在駐所檢察監督的基礎之上輔之以內部輪崗,并切實有效推進巡回檢察監督常態化機制,著力提升巡回檢察質效,以“派駐監督”輔助“巡回監督”,以“巡回監督”助力“派駐監督”。
在規范依據角度,應當著眼于刑事執行檢察監督范圍的廣泛性、復雜性,對監督范圍予以精簡,突出監督重點。對于監所內涉及生活、安全、學習的監管事項,檢察機關應當將著力點放在“監”,給予執行機關以寬松管理的空間,避免對其形成過多干涉。對于“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計分考核及獎懲”等執法事項,檢察機關著力點應當放在“督”,即督促執行機關嚴格依法履職,避免權力濫用或私相授受。
社會力量參與社區矯正的困境與出路
我國社區矯正工作歷經二十余年的開展,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截至今年6月底,全國累計接收社區矯正對象748.5萬人,累計解除矯正672.9萬人,現有社區矯正對象75.6萬人。全國共有5.8萬名社會工作者參與社區矯正工作。
社會工作者作為法定的社區矯正工作主體之一,在社區矯正實踐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取得了顯著的工作成效,已經成為社區矯正工作者隊伍中不可或缺的中堅力量。但是,隨著社區矯正工作的進一步發展,社會工作者也面臨著社會認同度低、角色定位不清、素質參差不齊、人員配比不等、工作隊伍不穩定等問題。
應立足我國國情,以社區矯正法為法律依據,結合我國社區矯正實踐狀況,采取強化宣傳引導、明確身份職權、規范人員管理、健全激勵機制、加強經費保障等針對性措施破解困境,以推進社區矯正領域規范化、專業化、職業化社會工作者隊伍建設,助力社區矯正工作持續有效推進。
2019年12月28日通過的社區矯正法從國家立法層面為社會工作者參與社區矯正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據,肯定了社會工作者的價值,也為社會工作者參與社區矯正工作的規范化、專業化、職業化發展指明了方向。
根據社區矯正法的規定,社會力量可以在社區矯正工作除執法權行使之外的各個方面發揮作用,包括參與組成矯正小組、制定并落實矯正方案、開展困難幫扶、教育幫扶、心理輔導、職業技能培訓、就業崗位幫扶、社會關系改善等。實踐中,“上海模式”“北京模式”“廣東模式”成為社會力量參與社區矯正的代表性模式。
筆者在調研的基礎上提出“心理咨詢師與司法社工相結合”的天津社區矯正模式。通過政府購買社工機構、心理咨詢機構等社會組織的司法社工和心理服務,由專職心理咨詢師向社區矯正對象提供專業的心理健康服務。社會組織向社區矯正機構派駐專職社工或專業心理咨詢師,開展心理測評、日常心理咨詢、教育幫扶等,將社區矯正心理服務和司法社會工作融入基層社會治理大局,積極開展心理團輔和社會幫扶,助力社區矯正對象的再社會化積累了寶貴經驗。
完備的刑事法律體系由三大支柱構成——實體性的刑法、程序性的刑事訴訟法和集實體性與程序性于一體的刑事執行法。
刑事訴訟法承擔的任務,最終要靠刑事執行來完成。鑒于此,刑事執行是相對于其他刑事司法活動而獨立存在的一項刑事司法活動。而承載刑事執行這種獨特地位的法律規范就是刑事執行法。刑事執行法承擔著懲罰和矯治罪犯、使其成為守法公民的特殊任務。
因此,刑事執行法與刑法、刑事訴訟法,理應具備同等的法律地位,應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立法作為國家的基本法律。筆者認為,在監獄法和社區矯正法的基礎之上編纂刑事執行法,才能實現刑事法律的整體平衡,確保刑事執行的權威性。
(作者系天津工業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犯罪學學會副會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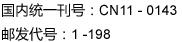
 微博
微博
 微信
微信





 京公網安備 11010502038778號
京公網安備 11010502038778號